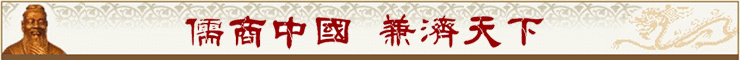“现代性”的社群主义视野:“儒家民主”如何可能?
(二)儒家民主模式 郝大维、安乐哲从“个人”、“共同体”、“人权”三方面构建了一个“儒家民主”的基本模型。他们既从历史的角度,也从现实的角度,对儒家式的“个人”、“共同体”、“人权”进行了分析和新的诠释。 第一,“中国式的个人”——“焦点/场域模式中的个人与社会” 古典中国传统设定人是某个行为者,而不是某个身份者。个人即是其如何在一个人的共同体环境下处事。个人秩序与社会秩序是相互包容的。如果使用焦点/场域的解释模式,那么“个人”就是指“具体的焦点”,家庭、社会与国家,甚至天下,都是“个人”这个“焦点”所在的“场域”。这个个人性的质素是在人的关系的“场域”中获得的。对中国人来说,和谐依然是支配性的标准。而这种和谐不是通过相互独立的个体的共同调整来取得的,而是个人在关系场域的焦距的实现。这种关系场域的和谐又是通过合适的焦点来获取的。自我实现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任务,自私的考虑阻碍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社会角色的质素聚合成为一个人的身份,也构成了这个人的自我。创立自我并不是扮演单纯的角色。而是扮演恰当的社会角色。人的概念作为具体的角色矩阵,不会容忍任何对于自然平等的宣称。这样被理解的人毫不动摇地站在等级关系之中,这种等级关系反应了他们之间的重大区别。对于平等的理解,儒教社会的与自由主义社会的是很不一样的。平等对于接受儒学的人(对于实用主义者也同样)来说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不是一个量的概念。在儒教社会里,人类特点的宽广连续体,被分成了互为补充的特性。儒学与实用主义都证实,个人自主性并不一定有益于人的尊严。事实上,如果尊严被感觉到是值得的,如果价值和意义与所投入的兴趣相关,那么个人性的夸大就可能成为保护和培育人的尊严的最终目的的可恶之敌。儒学和实用主义者都提倡对占支配地位的西方自主个人性的概念进行重新思考,二者所共享的关于人的社群主义的概念能够重振我们所有人对促进自我实现的承诺。 第二,“一个沟通的共同体”——“既非集体主义,也非个人主义的仪规(“礼”)的共同体” 儒家社会是一个通过仪规实践达到有效沟通的“仪规共同体”(ritual community)。作为共同体论说的仪规概念,包括所有不同的角色、关系和制度。这些东西固定并培育了共同体,它也包括了任何形式化了的、赋予意义的行为表现。这些行为表现把共同体内的人组织了起来。在个人的层面上,仪规使许多正式的环境成形,通过这些环境我们交流个人的经验。在共同体的层面上,仪规包含从家庭到政府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仪规也是语言,通过这种语言中华文化得以表述。虽然仪规实践最初用其惯常化了的形式导引人们进入社会关系,但是它们并不只是给予人们一个文化传统中积淀下来的合适行为举止的标准。仪规实践还有个人创意的一面。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更带有规劝性而不是禁止性。仪规的开放性构造使得它能够被人格化与重新构造以适应每个参与者的独特性与质素,这是任何正规的社会模式所不及的。从这个角度看,仪规又是一个有弹性的创造的实践体,用以登录、发展和展示每个人自己在文化上的特性。它是有教化功能的人们将真知灼见具体化的载体,使得人们能够从自己的独特角度来改革共同体。郝大维、安乐哲强调:“儒学对社会秩序的理解认为,个人与共同体的实现是相互依赖的。正因为这样,社会秩序不能以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两者必居其一的古典形式来理解。在西方支撑这两种观点的主要思想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可言。”[47]儒学中的“自我”并非定位很高或自成单体,而是一个角色与作用的复杂体。这些角色与作用又与一个人对其所属的各种群体组织的义务相联系。一个具体的人体现在人格化了的各种角色关系之中。郝大维、安乐哲认为离开了人的具体的角色环境,“构成一个有机个人的东西就不存在了:没有灵魂,没有头脑,没有自我意识,甚至‘我不知什么是,什么不是’(I know not what)。”[48] 第三,“社群社会环境中的人权” 中国传统上一直认为,“权利”是由社会给予的(这一点与实用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且这些权利是通过某种教育而得到弘扬的,教育的目的是让个人认识到自己对于个人间和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性。因此在传统中国,从法律上强调严格施行权利的倾向较小。事实上,依靠执行法律远非是实现人的尊严的一个手段,而是从根本上使人丧失人性,因为它导致相互适应的弱化,损坏共同体的具体责任,而这些责任对什么是合适的行为起界定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国人对权利的社群主义的理解会走向促进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促进个人的权利。权利绝对是以道德原则来界定的,而利益是与实用和社会福利相联系的。一旦社会福利得到重视,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维持,少数的利益则被放在了第二位。权利有时起的作用是保护少数人而不顾多数人。如果依助于利益就不会允许这种对少数人的保护。在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社会里,目标不是保护个人,而是将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融合起来。中国政府和除了极少数人之外的中国人民,都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国人关于人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共同体的承诺,这种情况下,由自由主义民主所渴望的“人权”就不被视为一种理想,而是一种病态。郝大维、安乐哲感叹地说:“当代人权问题争论的一个令人悲哀的特点是,人们花大量的精力试图去证明权利的精确地位与内容之所在。……至于我们如何去确保(从具体的条件出发)实施这些权利的机会,这些理论家们所剩的精力就比较少了。”[49]郝大维、安乐哲反对抽象地讨论人权,主张更多地关心人权的实施。用罗蒂的话来说就是,证明权利的基础必须在历史的共同体里去寻找,而且权利是在其中得以运用的。罗蒂清楚地意识到,光把人权两个字写出来并无任何价值。对于“做人意味着什么”,郝大维、安乐哲强调:儒家和实用主义都是从历史主义和文化主义角度来解读的。郝大维、安乐哲不无讽刺地指出,尽管有满口的启蒙运动辞藻(说所有可属人类者皆给予平等之地位),但从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来看,西方人没有完全把中国人当人看(也许中国人把西方人不当作人看的历史事实较少)。[50] 郝大维、安乐哲还对与儒家民主模式相关的重大问题,如性别与少数民族问题、公共领域问题、法制问题提出来进行了专门的分析。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对儒家民主来说是特别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儒家民主的实现必须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有创造性的回应。 第一,性别与少数民族问题 任何人只要到过儒教社会,就会认识到这种社会浸透着男子主义特征。在实际的层面,无论是从政治上讲,还是从道德上讲,男子主宰事实上在重要的程度导致把女性排除在成为完全的人的目标之外。中国人性别概念的特点是,如果——只是如果而已——女性像男性一样被允许有自由去追求充分实现自己抱负的目标的话,那么她也能够寻求一种人的同等气质的和谐。中国人的性别歧视,从传统上说就一直拒绝女子成为完全的人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性别模式对男子/女子的关系民主化有不能忽略的价值,与西方的模式相比,它可能更显得有人情味。当前,在西方文化中妇女的地位总的说来被认为比大多数亚洲社会中妇女正在争取到的地位要好。然而,成为完全的人的西方手段使得古老的男子特权永久化:要成为(完全的)人,你必须得看上去是男性。而儒学就如何获得两性真正平等(儒学要求女子要像一个女子,如果女性也被看作是一个完全的人话,那么她是作为一个女子而不是作为一个男子)这个问题上有一些值得学习之处,这也许使人感到惊奇。 妇女问题比起少数民族问题来,显得大有希望。中国对待少数民族是受这样一个因素左右的:赞同汉的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将此作为中国的突出特征。少数民族是分离开来的,而且鼓励他们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关系,与盎格鲁——欧洲人对待少数民族的区别是:在中国,民族与文化特征被置于显著地位的程度。与弱化民族与文化区别的做法相反,出现的一种试图赞颂这种区别的做法。困难的是,不像性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文化中,没有任何明显的模式可以支持汉族与非汉族关系的民主化。这一困难又因以下这个事实而加剧: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与美国相比是比较少的,因而内部几乎没有变革的压力。不过,儒学原则有一种最大的潜力,能够让事情向更好的方向转化。只要在儒教社会中向民主的过渡不仅仅只涉及到无情的政治与经济进程,那么人们完全可以希望这些特点(性别与民族关系民主化问题)会被考虑进去。在性别平等与少数民族问题上,郝大维、安乐哲明显具有西方式(美国式)的预设和偏好。 第二,公共领域问题 郝大维、安乐哲认为,在我们(西方)的传统中,单体的自我现象是后来才出现的。希腊文化的初期,社会组织的部落性质完全排除一种强烈的相异性。伴随城市的兴盛以及使得都市中心得以维系的商业关系,希腊人强化了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区分。将家庭亲密关系与公共生活中比较不具人格的关系分离开来,进一步促进了个人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在中国的情况却是大不相同的。古代中国克服伴随民族和文化多元论而来的矛盾与冲突的威胁,是借助于作为传播文化之媒介的语言,而不是借助于城市化进程。另外,中国人从来不强调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区分。因为家庭是所有关系类别的模型,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公共领域。但是郝大维、安乐哲声明,如果不是按照自由主义民主对公共领域的理解,而是按照实用主义的理解,我们就可以谈论中国的公共领域。郝大维、安乐哲强调了在多元社会公共领域存在的重要性。理由是:“(多元社会)会有互动的无穷无尽的复杂结构,从中引出种种间接的结果,而对于这种结果必须给予关注。”[51] 第三,法制问题 在中国,社会秩序一直被解释为一种和谐,它是通过个人参与一个仪规构成的共同体而取得的。因此,社会秩序的理想不能靠循着一套客观的法律或风俗来实现。看重法律被看成是承认共同体的失败,而远非将其高估为裁定社会冲突的合法资源。强调通过人格化了的仪规角色和关系来取得社会和谐,就使得中国人的仪规共同体与西方的法律社会(society of law)截然区分开来。也许受仪规左右的秩序与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之间的重要对比,是羞耻感的养成以及共同体从中得以确保的自我改正。中国不能简单地引进西方对“法制”的解释。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得法律的活力与中国人社会的道德之间脆弱的平衡更趋紧张。如果中国要从引进西方式的法律机制中获益的话,对这两种文化的历史具有某种意识是必要的。中国的历史发展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这就排除了能将法制轻易地移入一个儒教环境的可能。中国既不宣传统治者与公民之间有一种对抗关系,也不宣扬对于好的生活个人概念的多元。在西方对法制清晰理解的主要条件在中国并不存在。在中国,“法”的构建是与复杂的官僚结构的发展同步的,这种官僚结构起的作用主要是作为稳定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手段。就西方意义上的民法与刑法论,它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数量的增加和执行的时期,这都是在仪规行动作为一种约束力量丧失了某些效能时出现的情况。而且,这样的法律保护的不是公民,而是“社会秩序”。在西方,法律的起源是对专制权力的一种反映。法律所起的作用是保护公民不受国家、不受多数派人专横的侵害。在儒教中国,法律的构建是表述行政职责,在维持社会稳定中克服仪规的不足。在中国,法律的演化可以描述为是由“礼”移向“法”,再由“法”移向“刑”。不假思索地将西方法律机制移进当代中国,可能对约束共同体的社会义务带来重大的破坏。特别是,西方对法律的契约性质的理解在中国人那里几乎一直不被接受。法律在西方得到的评价是积极的,因为它与对权利的保护相联系。在儒家的中国,法律——从除了行政规则之外的任何意义上说——被视为一种仪规失败的象征,因为仪规未能够取得社会的和谐。这种失败从根本上说是道德的失败。 郝大维、安乐哲从近代以来中国宪政和宪法的实施历史得出了中国宪政和宪法不同于西方的五大特征,第一,中国的宪法不仅界定现行的社会政治秩序,而且也为进一步的成就提供了蓝图,有如美国的“政党纲领”,而不是美国的宪法。第二,中国的宪法不对制定宪法设定界线。第三,中国宪法与其说是一个政治文件,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文件,其基本的功能是促进社会的和谐,而不是保障公民的权利。第四,中国的宪法不是立法的依据,而主要是使地位、特权和义务定型化。中国宪法基本上是一个合作的协议,这个协议又是基于个人与共同体相互之间的信任,而不是潜在内抗力量之间的契约,所以就没有独立的条款来保证实施个人对国家(机关)的反对主张。第五,中国宪法的最后一个特征是,权利完全是从一个人作为社会一员的资格派生出来的规矩,而不是个人的拥有品。这些规矩主要表述为社会福利的享受权,而不是个人的政治权利。由于人只是“社会人”,不参与到共同体中去,就失去了自己考虑权利的资格。这点从中国宪法中权利与义务不可分上可以反映出来。这五大特征其实是否定了中国所谓的宪政和宪法是西方意义上的宪政和宪法,中国的宪政和宪法深深地打上了儒教中国的特征。郝大维、安乐哲认为:“对法制过分地抱有信心,对维持社会秩序的非正规机制一味地抱猜疑的态度,就会使我们很难领悟这一不同的儒学模式。”[52] 结语 郝大维、安乐哲对民主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两分法理解,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民主的复杂内涵,在此不论。但作为一种研究取向,无疑给我们的政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创新性的启发。两位作者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民主的复杂前提是可取的,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辨证过程。有着2000多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其“儒家式的民主”是否可能?是否可欲?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反思的问题。作为非中国文化传统的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与政治现代化关系的反思是否妥帖,是否到位,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从另一种文化的眼光看中国,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被遮蔽掉的一些问题,尤其可以相对客观地进行观察和思考。还有,作为异文化学者,对中国文化孜孜不倦的研究,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高度关注,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当然,郝大维、安乐哲并不是纯然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也在寻求解决“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药方,并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沟通的社会而努力。郝大维、安乐哲对自由主义民主和社群主义民主的大体看法是,自由主义民主认为个人的权利先于社会组织且独立于社会组织而存在,因此个人权利高于社会权利(指共同体的权利),而社会权利则来自个人权利的让渡或者说是个人的授权(通称“社会契约”),个人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达到自我完善,美好的生活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严格区分的,个人对共同体的和谐和完善没有建设的义务;社群主义民主认为个人的权利是从社会中来,个人权利的实现同样有赖于社会的沟通和共识,个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认同是在社会之中完成的,个人社会化(认同共同体并与之互动)的过程也就是个人的自我成长和自我认同的过程。美好生活的实现有赖于共同体的理解、沟通与建设,共同体不是一个僵化的对个人进行窒息和封闭的团体,而是一个个人与个人互动的开放的体系。郝大维、安乐哲认为,前者是本质主义的理解,后者是历史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理解。他们赞同后者对民主的诠释,并且认定亚洲儒学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共享社群主义的民主资源,以此为基础,中国和美国可能开出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的社群主义民主来。在现代性面临着种种“危机”的时刻,美国新实用主义和亚洲与美国的新儒学的兴起以及平等对话,也包括各国各种文化资源的平等对话,将有利于这个世界的文明创新和和平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自由主义民主与社群主义民主既是民主的两个极端,也是民主的一体两面。个人权利与共同体权利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个人或共同体造成不可挽回的“异化”,甚至伤害。两者的反思平衡可能才能满足人类最深层的不同需要。据美国历史学家、亚洲学家艾恺先生观察,“人类本性存在着深邃的两面性和暧昧性。(自由主义)民主与平等之“好”是不能否认的;而其“坏”的效果也是无可否定的。它们恰恰是同一状态的体现。”个人权利的过度强调必然的后果是个人相对于共同体的日益“离异化”和“失常化”,否则个人得不到自由主义的自我认同,艾恺强调:“‘失常’乃是个人自由的根本性质,也是它的代价,现代生活,其非个人性,缺乏恒常的人际纽带,没有道德准则或道德的确定性,欠缺主体认同等等,恰恰是个人自由和解放的终极状态。”[53]当然,过分强调共同体的权利也会造成对个人的伤害(如哈耶可所痛恨的“多数人的暴政”等),甚至共同体同样也会产生相对于个人的“异化”(即共同体本身的日益“官僚化”和“非人化”)。自由主义民主与社群主义民主的冲突乃是人类两组基本欲求的冲突,不但象征和表达了人类最深的社会冲突,也象征和表现了人性本身的深邃矛盾。 [1] 郝大维(David L. Hall),文化哲学家,美国的中国学家,已故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哲学教授。著有《经验的文明:一种怀特海式的文化理论》(The Civilization of Experience,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73)、《多变的凤凰——朝向后文化感性的探索》(Uncertain Phoenix:Adventures toward of Post—Cultural Sensibility,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82)、《爱欲与反讽——哲学无政府主义绪论》(Eros and Irony:A Prelude to Philosophical Anarchism,Albany:The State U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2)等,与安乐哲合著有《孔子哲学思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预期中国》(Anticipating China,1995)、《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1998),皆由the State U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出版。关于亚洲与中国问题的论文有《亚洲与美国的文化遭遇:现代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1997)、《中国、杜威及先贤的民主》(1997)、《第二眼相爱:儒学与实用主义的再汇合》(1998)等。 [2] 安乐哲(Roger T. Ames),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学与比较哲学教授。著有(与罗思文)《孔子的论语:一种哲学翻译》(Roger T. Ames and Jr. Henry Rosemont: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New York:Ballantine,1998)、与郝大维合著有《孔子哲学思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预期中国》(Anticipating China,1995)、《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1998)等。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有《反思儒家自我:对芬格莱特的回应》(1991)、《经典儒学中的焦点/场域自我》(1994)、《继续有关中国人权的对话》(1997)等。 [3]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Chicago ﹠Lasalle,Illinis:Open Court,1999. [4] 关于郝大维的文化哲学体系和对文化哲学的贡献可以参考美国中国学家、“波士顿儒学”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南乐山(现任波士顿大学教授)的《文化哲学家郝大维》,还可以参考美国“新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理查德·罗蒂(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的《浪漫主义者、智者和体系哲学家》,两文均见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附录),何刚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先贤的民主》。 [5] 南乐山认为,在郝大维那里,“文化哲学”取代了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现代欧洲的认识论,成为“第一哲学”(Fist Philosophy)。郝大维的“文化哲学”崇尚建构与综合(通过类比),而非辨证与分析。参考南乐山的《文化哲学家郝大维》,见《先贤的民主》附录,第217——218页。 [6] [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14页。 [7]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17——18页。 [8]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18——25页。 [9]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26——27页。 [10]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28页。 [11]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35页。 [12] 中国历史学家、已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荣渠教授主张,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不是一元单线论,而是一元多线论。他说:“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我们称之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元论。但是,‘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参考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施密特》)”。见《一元多线历史观——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参考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13] “亚洲(或中国)中心观”(从亚洲或中国视觉来分析亚洲或中国现代化历史)的代表性历史学家除了保罗·柯文,还有《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有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年版,中译本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和2001年版刘北成译本)一书的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和《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有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版,中译本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史建云译本)一书的作者彭慕兰等。 [14] 参考[美]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5]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35——40页。 [16] 李泽厚先生认为,“体”指本体、实质、原则(Body,Substance,Principle),“用”指运应、功能、使用(Use,Function,Application)。他说他的“西体中用”论是针对“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亦即“西体西用”)而提出的。他强调,某些论者故意避开“中”、“西”、“体”、“用”,或提出“中西互为体用”论,或提出“中外为体,中外为用”论等等。表面看来,十分公允,实际上等于什么话也没说,而恰恰是把现代与传统这个尖锐矛盾从语言中消解掉了。关于“西体中用”说可以参考李泽厚的《再说“西体中用”》,《原道》(第三辑),1995年4月。 [17]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32——34页。 [18]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29页。 [19]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19页。 [20]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25——26页。 [21]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29页。 [22]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31页。 [23]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27页。 [24]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42——43页。 [25]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44——47页。 [26] [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47页。 [27] [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47页。 [28]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93页。 [29] 郝大维、安乐哲认为,美国的实用主义被一些欧洲和亚洲的思想家嘲弄过,他们把实用主义视为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法性思维,因而毫无疑问地不是理智的,也根本谈不上精致。实用主义被一些哲学上孤陋寡闻的人错误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和技术狂热的一种简单分支,他们往往把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美国人的事情就是做生意”(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视为是对实用主义的经典诠释。实用主义因而给人留下了怪异的印象。其实,在美国,实用主义是一直被边缘化的。只是到最近,新实用主义才全面地恢复了对实用主义的兴趣。参考《先贤的民主》,第77——78页。 [30]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58页。 [31]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59——60页。 [32] 参考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59页。 [34]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61——62页。 [35]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62——67页。 [36]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69页。 [37]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73页。 [38] “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是由古典儒学发展而来,“理学”(Neo—Confucianism)也包含在古典儒学的范畴内。郝大维、安乐哲认为,对儒学应持一种叙事性(narrative)而非分析性(analytical)的理解。他们认为对儒学的分析性理解,易于将儒学本质化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一种技术哲学,一种系统哲学,结果把儒学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形式化和认知性的结构。而儒学根本就是一种审美性与叙事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将每一种境遇的独特性作为前提,并且,在那种传统中,礼仪化生活的目标是将注意力重新导向具体情感的层面。儒学是一个社群的连续叙事,是一种进行着的思想与生活之道的中心,不是一套可以抽离的学说或者对于一种特定信仰结构的信守。作为一种连续文化与生活叙事的儒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周而复始、连续不断并且始终随机应变的传统。即活的生活传统。从这一传统中,形成了它自身的价值和理路。因此,儒学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传记性(biographical)和谱系性(genealogical)的,它是对一种形成性典范(formative models)的叙述。参考安乐哲:《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一种对话》,见《先贤的民主》附录,第163——164页。 [39]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81——82页。 [40] “新实用主义”的诞生,主要以里查德·罗蒂1979年出版了《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为标志。在该书中,罗蒂大量吸收并创造性发展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罗蒂认为,杜威的思想主导着对美国实用主义的任何一种理解。杜威在美国被公认为实用主义文化传统的诠释者和实用主义文化哲学的奠基人,并被称为“美国的孔子”。安乐哲说,自称是“美国”哲学家的怀特海(A.N.Whitehead)说过:“如果你想了解孔子,去读杜威;如果你想了解杜威,去读孔子。”参考安乐哲:《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一种对话》,见《先贤的民主》附录。郝大维、安乐哲还认为,早在1920年,杜威在被中国一所大学授予一个名誉学位时,被誉为“孔子二世”(Second Confucius)。参考《先贤的民主》,第74页。 [41]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82页。 [42]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77页。 [43]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78——79页。 [44]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1页。 [45] 弗兰西斯·福山实际上是认可自由主义民主所谓的“民主”纯粹是量的概念。他虽然欢呼自由主义民主在全球的胜利,并认为这可能是“历史的终结”。但他不无忧虑地认为,自由主义民主的最终结果是一个“人人平等,个个相同” 却“没有抱负,没有理想”的“最后之人”组成的社会出现,虽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可这个问题”,却是“让奴隶和一种奴隶道德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他认为这种社会并不适合人类居住,“最后之人”有可能由于精神仍然未能得到完全满足而重返霍布斯和黑格尔所称的“为荣誉而血腥战斗”的“最初之人”。福山认为,亚洲价值的“优越意识”(即“等级意识”)最终会构成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最大威胁。不过,福山肯定地说,从长远看,自由民主国家存在着从内部被颠覆的可能,其罪魁祸首不是过度的“优越意识”就是过度的“平等意识”,即对平等认可的狂热欲望。他说,我的直觉是,后者最后对民主的威胁更大。一个文明如果沉湎于一发不可收拾的“平等意识”而且狂热地追求消灭所有不平等,必定很快就会陷入自然本身所设定的框框之中。参考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6]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92页。 [47] [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129页。 [48] [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129页。 [49] [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146——147页。 [50] 参考[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149页。 [51] [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131页。 [52] [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第137页。 [53] 参考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 上一篇:孔门弟子:蔡德贵
- 下一篇:《中庸》新论:哲学与宗教性的诠释(安乐哲)
-
请您注意:
- ·自觉遵守:爱国、守法、自律、真实、文明的原则:《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