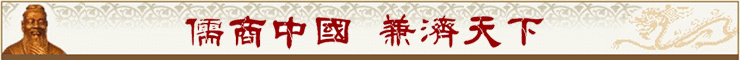好古育德,恶古祸民——《论语》心得之二(钭东星)
《述而·二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犹言汲汲,勤快。焦循《论语补疏》则引《左·僖公卅三年传》注谓:“敏,审当于事。”亦通)而求之者也。”
附] 《易·大畜·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述而·一》
子曰:“述而不作(传述阐发而不敢蔑古别造),信而好古(汉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即此句之义),窃(暗自)比于我老彭(汉包咸《注》:老彭,殷贤大夫,好述古事)。”
附] 陆贾《新语·术事》:“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故设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
【孔子关心的这个“古”非一去不返的往事,是中华民族赖以安生保国的“古道”,学古修身,以崇其德而已。四千年的文明史,至近百年遭到最残暴的毁灭,祸巨毒深,应该反省了!
一、这两章中,孔子明确表示自己对民族历史的态度是“好古”。前章说,我之所知都源于古,敏求而后得,非不学自懂的“生而知之者”。后章言我愿效前贤,学术阐述往圣而不敢蔑弃古贤,妄作史无前例之举。“作”朱熹《论语集注》曰:“创始”,是于古无据,师心自任,实指自造全新社会文化制度强加天下。古人认为“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如周公就能制礼作乐,孔子有德无位,只能敏求三道治道之共同原理,思想道德虽自成一系统,而德政礼治之社会体制,终止于阐述本义以批判滛奢腐败,而不曾以私意自造主义强加天下。“不作”当然不是老庄之“无为”“无我”,孔子一生勤勉好学,温故知新,晚年删(订正)《诗》《书》、订《礼》《乐》、赞(阐明)《易》、修《春秋》,几乎传述了所有古代经典,然后成吾道一贯,溯其本源则非创始,“述”古而已。班固言:“皆因近圣之事(唐虞以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汉书·儒林传叙》)述与作的关系,大体谓事本于三代传统,道得于吾学而思,弘先王之教非自我作古,是孔子的自我定位。李《读》把“不作”解为“不发明创造”,是概念混乱:人能制器,不能制道;礼由人废立,而礼之元理为人性之道,是天生的客观存在,非由学者任意创造或抹杀之物也。至于“发明”,今谓器物之自无而有;古谓事理之隐而未显者,阐发而明白之,义等于“弘明显扬”。孔子弘明仁义之功,有力于“信而好”的自白,尤宜深味:“信”为言之诚,古人不诬我,史必有事、事必有故;“好”则不独知古而己,见贤思齐、不善而戒,以古之得失进德修业也。与现代逞私智“疑古蔑古”,自命超迈前贤之学风,截然相反!
孔子“好古”一语,百年来视同大罪,受到无数批判与恶意嘲弄。李零于这二章,一则曰:“好学学什么?学古代。”二则曰:“孔子是个复古主义者。”都一言以嗤之。而大谈老彭、神仙、房中术,特意推销自己的二本书冒充新知,却与《论语》毫不相干。蔡《导》列《论语》糟粕十四项,以“复古开倒车”为首罪。释本章云:主要是好西周之古。同为几代学者恶古之武断。百年持续诬古迷新之狂热,乱正道惑人心,必须重头反省:好古与恶古,孰利中华民族生存?孔之“好古”,无非是珍惜热爱古人留下的仁义传统以救乱世生民,这与要求退回原始生存状态之“复古”(如《老子》《庄子》)全然不同,更非批孔运动家谎称的“复辟”。孔子少也贱,由自学奋斗成“哲人”“国老”,没有失去的“辟”(君位)可复。三代礼文“吾从周”,从未反对文明进步;只因人世无道才求变革(“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变齐变鲁,以仁义推动前进,所以需从三代人文传统中汲取仁智本源。世事有古今之殊,仁道无新旧之异。“三代之礼,一也(本质贯通),民共由之。”“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可述而多学也。”(《礼记·礼器》)如亲睦是生之本、忠信为友之本、仁义乃正治之本,皆通古今天下之人道根本。一国政教,不忘本而人心有德,国家始有正道可立。一个民族,珍惜自己的好传统才能不亡于世界之林。今日盛言“爱中华”,却不知中华历史文化有何可爱处,何来由衷之情,奋发之志,肯为民族安乐竭诚尽力?甘于忘本而恶古,对中华无知而热衷于媚洋鄙华,学者数洋典而忘本祖,天天高叫“爱祖国爱中华”者,岂非欺心之谈?百年前龚自珍考察古史变迁后,得一结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祖宗、败人纲纪,绝人之材,无不“必先去其史!”孔子好古之时,正当中华斯文危机之际,“天之生孔子,不后周不先周也,存亡续绝,俾枢纽也。”(《古史钩沈论》)清末民初的革命家即使非圣,仍爱民族,熟读历史。章太炎教育青年云:“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章太炎全集》册四《答铁铮》)五四后近百年,乃盛行以洋主义丑诋民族,邪说暴行并作祸民。何况以史为镜,足以减少改革中的大量谬妄。我族历四千年无数灾劫而种性未泯、文化长存者,孔子“好古”之教有大力焉。
然而“好古”目的为育德,不可笼统当口号推行仿古。古史是精华糟粕同时浮沉的长河,现代亦文明野蛮并呈之世界,古今中外俱非“进步”“落后”一词可尽。“厚古”“迷新”二派,俱以时间先后定理之是非,其谬相等。如在大批特批孔子“好古罪”的同时,又大吹大捧二千年前韩非的权术与秦政之暴虐,就不嫌其古了。孔子一介布衣之士,虽无辟可复;拥有天下最高权力与最毒治术的秦皇帝制,却极易借尸还魂,“复辟开倒车”!故今人首先要问:“好古”是好其仁政爱民的思想精华,还是好君主专制的恶政传统?“厚今”是倡导社会仁道公正的潮流,还是煽动权贵专横暴虐、富豪自由弱肉强食?这才是古今所同的真问题。
好古之价值,视学者道德之高下。孔子志于安乐天下的仁道,于古独专心于仁义之理源。《论语》为学屡言“博文”,其时存世的古文材料尚博,至今散见各书称引的如《夏训》(《左·襄四年传》)、《故志》《训典》(《国语·楚语上》)、《典图刑法》(《国语·周语下》)、墨子所言“百国《春秋》”,和晋时盗发汲冢魏墓出土的一大批古文书等。凡能见到,必在夫子好古博文之内,见善则师,古学决不限六经,仅本书各章附录,足可为证。汉清经师,以为《论语》每义都从《周礼》《春秋》出,至今奉为学术正宗。岂知哲人之博古深思,取精用宏,非专抱一经当饭碗之学者可比拟。
孔子“好古”,所以“敏而求之”。求什么?求先王政教所以协和万邦之道与使天下老安、少怀、朋友忠信之德,非食古不化的记诵知古。“敏”“求”二字关系得之多寡、知之深浅,至切至要,最宜紧记。敏则求知若渴、思维兴奋、直觉活跃、明辨而当,故能事半而功倍,所见自真,心得自富。求索的工夫最艰辛,去粗取精择其善,由表及里求其本,由此及彼寻联贯,从个别而明一般,下学上达,自纷杂人事进而探索天性本原,终于形成哲人心中的一贯之道,乃始立生民未有之仁学与人格。人所思想,无不凭籍已有资料。“人能弘道”,不能造道。不好古即无好学,学而不思、无得于身,则“道非弘人”;吾独好学深思,敏求而得,此一述古之新知,虽谓之“吾道”可也。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朱熹指出:“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也。”记三代古事之经传虽珍贵,终不及以仁道教化千秋之功用更伟大。人皆知夫子以“诗书礼乐为教”,而所教与汉儒至今的章句鄙儒大不相同。可惜《论语》鲜录夫子读书自得之例,需参见它书,如近年出土战国楚墓竹书《孔子诗论》残简,犹可见一鳞半爪。《尚书大传》载:子夏读《书》毕,见于夫子,谈心得。夫子指出其“见其表,未见其里”,指导说:“丘尝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则前有高岸,后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六誓》(此与下《五诰》皆《尚书》篇目之简称)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美政)。”可知夫子悉心致志于诘屈聱牙的《书经》之中,务求从文句进入先王处于前有高岸、后有大溪之际的决策思路,发现“正立而已”,这一君德,正是为政之道!析而言之,《书》篇各有重点,“七观”即以述为作之佳例。好古是动力,敏求是途径,温故而知新则可为师矣。“学为已”而后道为人,好古出新,述通于作,才是文化继承、历史发展的唯一正道。其新有本,所作信而有征,故世人信服而乐从。先秦乃至整个古文明世界都出过一批杰出思想家,独孔子述作的根最深,土最厚,入人之心最深,其源远故流长,历经二千五百余年颠扑而不破。国学真髓在此,中华灵魂在此。《论语》不但“鸳鸯绣出从教看”,好古敏求四字,又把自己一生由少贱而成哲人的“金针度与人”矣。
二、可惜“信而好古”了二千余年之正统儒学,实以经学代孔教,严重偏离孔子终生敏求的仁义大道。荀子所谓“隆礼”,竭力尊君主权力体制至高无上,贱《诗》《书》之仁义。汉袭秦制,学宗荀子。太史公曰“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汉书·儒林传序》云:“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史官代表王朝立论,是汉人普遍视孔儒只是传经文之经师。自从汉武帝定下“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的方针,至今误传汉武“独尊儒术”就是孔学独尊。其实汉人所谓“儒,术士之称。”(《说文解字》)泛指各种学术道艺。《汉书·艺文志》辑录刘向父子的《七略》,将天下古今所有图书(六经、诸子、诗赋、兵法、天文、历谱、蓍龟、杂占、相法、数术、医经、房中、神仙、方技等)全笼其内,都当“王官”职事之学的一支流,故各种道术之士皆得称儒矣。以此“独尊”,实无所不尊。不过汉廷“表章”,只有六经,故二千年间尊为“经典大法”者只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种先王治世大法之典,汉武为之各立博士官,配弟子授学,只不过继承秦制行霸道法术时“缘饰(若衣之绣花镶边)以儒术”,当作朝廷稽古右文的盛事。从《汉书·艺文志》可知,《论语》《孟子》不在“经”中,不列官学,孔创之“儒家”位等一家言的诸子,用同解经的“传记”,仅因说经胜过诸子它家。汉唐君臣,《论语》与《老子》并习,甚至孔子、老子同祭。“孔子专制”压抑思想自由,纯属子虚乌有。汉武所用多酷吏,所行类秦政,一生忙于扩张帝国领土扬声威,国民死了一半亦不惜。虽然接受董仲舒建议以儒兴学,开办各级学校,而“是时,上(汉武)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汉书·礼乐志二》)孔子何尝“独尊”?秦汉以降的朝廷从来没有、也无法将孔子的仁道德政,当作指导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思想理论。程、朱每痛:“孔子之道,未尝一日行天下也。”在汉武尊了半个世纪所谓儒之后,为全国的盐铁是否应该收归国营,朝廷与民间进行过几十次激烈争辩,当权派全是申、商、韩法术权势家富官强兵之言,而在野贤良学者一致以孔子仁政爱民相抗争,最清楚地表明孔道真传在野不在朝(参见《盐铁论》)。西汉鸿儒好六经之古,旨在君尊臣卑、强干弱枝建立“大一统论”;东汉谶纬而外,饱学宿儒则专心经文字义名物的训诂,释字而忘义。汉代“儒学”之功,终于沦为说文解字的“小学”。东汉至清,儒学内部起异端之争,今古文相攻不休,集中在《春秋》上。古文派专求一字一句之古义,有似乎“述”。今文派于经无明据,凭“先师口说”造出孔子自命素王、为汉世创制新法等一大套隐而不书的“微言大义”,以为真孔独传,公羊家是也。今文之新“作”与古文之“述”古,两端皆主君权大一统,同悖孔孟仁义救民之大义。“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蜕化为不弘思想大义、专治训诂小道的学术风气,从汉儒奠定,至清代乾嘉诸儒总成,至今评审学术,牢不可破。以至二千年来虽代有勤苦的“学问”家,却少见先秦那群敏求天下大道的思想家。其间只有宋儒程朱等人,才把《论语》《孟子》与《礼记》中传孔孟之学的二篇(《大学》《中庸》)尊为经典,思辨失去血肉的《四书》理义之学。不幸生前以“伪学”遭权奸厉禁,元代中期以后被官方利用为考试标准,至清经师又以小学破碎大道,义理未获深入发展而终寝。中国经学长期专攻无思想之小学,百年来将尊孔读经同视作洪水猛兽;遂使中国君权专制意识形态也特别长寿。
清初颜元尝曰:“汉宋之儒,但见孔子叙《书》、传《礼》、删《诗》、正《乐》、系《易》、作《春秋》,误认纂修文字是圣人,则我传述注解便是贤人,读之熟、讲之明、会作书文者,皆圣人之徒矣。遂合二千年成一虚花无用之局。”(《四书正误》卷三)圣人非圣在“信而好古”上,皇清老儒动辄言“圣人著六经以垂万世之教”,实似是而非,孔子已声明自己“不作”六经,孔门垂教后人者为《论语》《家语》《孟子》《礼记》以仁道德政济民之困。仅熟读、注解、编写任何古典圣经,都不能证明自己是圣徒。圣人圣在心怀天下,为社会公正人人安乐而汲取古今历史智慧,以求历史出路,才能冲破文化“虚花无用”的局面。这是学术史上一个极深刻的教训,但愿有识之士能记取。
三、中华是地球上唯一有自足生存系统、五千年乱而未废的文明古国,儒学蜕变而外,古今尝历两度大劫难。昔为三代之道坏而权势专横兴,孔子指出祸根在权贵贪婪淫暴,败坏周礼(详后《季氏·二》义说·四);二十世纪持续汹涌的诬国史、蔑族性狂潮,则自文化精英煽惑知青而起,直欲彻底根绝民族种性,至今甚嚣尘上,国运民生难卜。学术界随世风而变,始而疑古,进而诬圣,终于以霸权打倒一切传统文化(只留刑政法术一家)。纵观全球,也只有中国现代文化奉反传统为“精英”。察其论据,不外持“三必”推行“三凡是”:今必胜古,洋必胜土,少必胜老。
①是土产祖传的秦政以刑法杀人灭文。理据见于《商君书·开塞》《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论”,谓当今最大权力即最高真理。荀卿弟子丞相李斯将时之古今宣判为理之邪正,势不两立,危言“道古以害今”,仁义古道是今帝极权之大患。始皇帝于是下令“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被历史咒骂了二千多年后,“五四”重又“打倒孔家店”、“不读古书”喊声震天,直至不断发动批斗“厚古薄今罪”,以打砸抢“破四旧”,北师大红卫兵高喊“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冲进孔府砸孔庙,挖孔坟,抢劫国宝,抬尸游行,广发《批孔战报》,号召全国仿效……这还是批孔批林运动之前。逻辑很简单:凡今即万岁,凡古该万死。
②古既一团黑暗,今实不如列强,于是假洋鬼子的崇洋神话应运而生:不问古今,“凡洋皆先进科学,凡华净愚昧落后。”故只有全面彻底殖民地化才能新生中国。启蒙教头们从师法东洋转而效美欧,又革命为全仿苏联,复改为与美国一体化。虽波诡云谲,血涂川原,皆名曰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之“现代化”。化得官专政,商专利,文瞒骗,人人争利相残;天丧清明,地污山水,国无忠信,而依旧歌舞升平。唯哀哀之民,非毒无可食,不辱无以生,居无定所,妻儿不保,老不得安,民族传统被彻底颠覆,道德荡然无存。连《论语》也广播成教训贫贱苍生“保持内心幸福”之物,孔亦非孔,圣智变为腐臭,则文痞奉为精英。
③百年以洋灭华之文化烈火燎原而焦土,急先锋皆几代世事无知之知青,煽动者为少数启蒙救世主,亦事出有因。1840年英人以船坚炮利打开满清禁鸦片之国门,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倡洋务用西学补中体之士,御外侮未以中华文化为敌也。至1894年甲午海战败于日本后情形大变,梁启超言:“我支那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后始。一战而觉四千年之文明原是南柯一梦,信心大摇。而日本政治思想领袖在我东北又战败沙俄后,野心大增,鼓吹以日为盟主建立“大黄种帝国”“让日本之旭日旗给人类以光芒”,举国激情昂扬。流亡、留学东洋之反清志士深受鼓舞,甲午战败不以为耻反视为幸(只要有利排满就好,“革命逻辑”每如此)。拼命兜售日人各类论著,大批使用日人译欧新词语,追求与日女联姻,皆最先进之表现。日本舆论谓中国为“野蛮、非理、丑陋、堕落”之国,日中之间是“自由与专制、希望与回顾、进取与退守”之本质对立,两者不能共存;“今日支那实早已灭亡”,侵华是先进文明对“残骸蠢动”之“义战”!由反清激进至彻底反中华文化的革命志士莫不响应,“中日亲善”,在两国先进文化人中热火朝天。日人胜而骄,给本民族列出“十大特质,尽善无恶。”其中不乏分明是仿效中华始有者。作为对照,竭力搜罗中国人的种种劣性,辛亥革命后内田作《支那论》总结道:“世界之国民中,其性情之恶劣如支那之国民者,稀也。”其驻清公使亦公言“支那人秉性之恶端”多至十种。证明中国当亡,种族应灭。而大批维新革命、著名学人乃至绅士、佛徒等生性鄙视庶民之中国精英,纷然参与灭华诬民的中日大合唱,至有同一事在日为优在华则劣(如家之伦理)。反华诬民中最激烈、最坚决、最彻底者,受封为“无产阶级圣人鲁迅”。鲁迅的思想奠定于留日时期,极端仇古之性本近韩非,至死不少易,所创专事冷嘲不作论述的战斗文风,代代知青效尤不绝。日人论优劣,主要指清末民初之国与民,如1924年内滕《新支那论》扬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理应灭中国,“然其(中国)于郁郁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日人并不否定“衣冠唐制度,文物汉宫仪”是中国历史文化对日本“莫大的恩惠。”鲁迅又大过之,对中国全部郁郁乎文皆恨入骨髓,五千年人文教化皆“吃人的筵席”,全部国史只“吃人”二字,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捏造成一“阿桂”,非唯教青年“不读中国古书”,连文字亦该死:“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中国孩子也不如日本的可爱……一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议论中国人与文,只知“痛打落水”的仁义道德、不见民族之一点可爱!其成名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之旨趣,亦拾自日人“中国国民性”“支那特质”的东洋灭华高论,杂文论国人不离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气质》胪列的二十六项,往往用词都不变。(详参王康《抗日胜利60周年断想》,“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七期)鲁迅卒于1936年,次年日寇即大举全面侵华,中国军民八年浴血抗战之惨烈,气壮山河,国史仅见,粉碎了启蒙者对国民劣性之诬!而以改造国民著名的革命文化家如汪精卫、周作人、周佛海、陈公博等纷纷出任汉奸要职,助敌灭华,至今有追捧少谴责,尤为五千年闻所未闻!盖民聚族而居,依国土而生,天生爱其祖国。而现代文化人沽名,故贵主义而鄙民性;主义无国界,只讲同志不问敌我,所以恬然当汉奸,卖国而不耻。至今文化精英以主义沽名谋利如旧,故绝不反思,若无其事然。蚁民只有默默领受精英无休止的咒生骂死,“现代”以“先进”吃人不吐骨,连罪名都听不懂!
讨厌学古,自行其是,孔门亦尝有人。子路提出:“请释(放弃)古之道而行由(子路)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东夷之子慕诸夏之礼,有女而寡,为纳私婿,终身不嫁。嫁则不嫁矣,然非清节之义也。苍梧之弟,娶妻而美,让与其兄。让则让矣,然非礼之让也。今汝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乎?”(《家语·六本》《说苑·建本》)洋人学说有其生成土让、演化历史与得失利弊,不知其本而崇洋如神,安知非假洋鬼子卖椟而还珠、兜售洋垃圾以病我中华乎?《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非拿山石毁宝玉也。如何学外国?恩格斯有明训:“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别的道路是没有的。”(《马恩选集卷四》P458)中国的百年痛深创巨,文化谬误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教导曰:本国痛苦是最好的学习材料。】
-
请您注意:
- ·自觉遵守:爱国、守法、自律、真实、文明的原则:《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