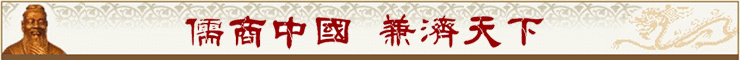从孔子与柏拉图对诗歌艺术的不同态度看两级社会的不同艺术思想(柚声)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相当孔子位置的有两个人,即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没有留下文字的东西,我们从孔子弟子们编撰的《论语》了解孔子,我们从柏拉图著作来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第一代弟子。柏拉图相当《论语》的编撰者们。柏拉图的许多著作是以苏格拉底与他人对话的形式写成的,无法分清哪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哪是柏拉图的思想。孟子与孔子隔了至少三代人,孟子与孔子分别生活在战国与春秋两个不同时代,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是同一时代的人。总之,孔子与柏拉图对诗歌等艺术的不同态度有可比性。他们这种不同态度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实质性差异,直接反应了他们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显示艺术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有着不同的地位与功能。
一、孔子与柏拉图对待诗歌的不同态度
这里首先要指出,受时代的限制,孔子、柏拉图讲的主要是诗歌与音乐,但他们的思想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古代诗歌与音乐不分,诗歌总是用来演唱的,而演唱就是舞台表演艺术,而舞台表演当然包括视觉艺术在内。古希腊绘画、雕塑很发达,中国相应较差,但它们对人类思想行为的影响远较诗歌艺术弱,所以孔子、柏拉图主要讲了诗歌。在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上,文字艺术远较其他艺术形式有力。
孔子非常注重诗歌音乐对人的教化作用,但并不象现代政治家那样把诗歌音乐看作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一种载体,孔子把诗歌音乐当成人生、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机成分来对待。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说,“先秦诗歌与原始巫术、歌舞密不可分”。[1] 我们可以设想,夏商周三代的统治阶级也继承了这一诗歌艺术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思想。孔子曾多次叫儿子伯鱼学诗,一次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一个人不学诗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他又对自己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孔子这里强调学诗可以激发人的志气,可以提高人的观察能力,可以加强人的团结与友好,可以抒发怨恨之情,可以用来侍奉父母、服侍君王。这些话都说明诗歌音乐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而孔子又如何重视诗歌和音乐。如果我们感到难以理解孔子这些话,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典型的二级社会,与孔子所处社会有本质的不同。
《论语·泰伯》里记载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记·孔子闲居》也提到孔子说过类似的话,“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孔子这里把诗、礼、乐看成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就是用诗歌激发和表达一个人的志气,而这种志气要礼来确立、乐来完成。这里孔子讲得很清楚,人类志气的表达、确立、完成,全部过程不涉及任何物质利益与功利成分,是一种社会和谐的美。这也就是老子所讲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人类志气所指是美化现有的生活,并非要求更多,更非掠夺他人的。
《礼记·经解篇》记载孔子话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这里孔子用诗教来概括一个人民的文化与风气:自乐其乐,和谐有序。近年来发现的楚国竹简《孔子诗论》几乎对《诗经》每一首诗都有评论,进一步证实了孔子将诗歌音乐当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来看待的观点。写于西汉的《毛诗序》总结这种思想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明确地表明诗歌音乐是人类情感的自然表达,而这自然表达的诗歌音乐却担当重要社会功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情感很难衡量,更无法度量,所以这种用情感建造与维系的社会只能是原初社会,二级社会是建筑在理性之上的,感情在理性的控制之下。
古希腊处在战争文明的早期,如果他们也像孔子那样仅仅追求和谐与美的话,就成了别人的刀下鬼,所以古希腊一定要追求功利,也同时需要铁的纪律。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以苏格拉底与他人对话的形式长篇论述艺术对人的影响以及国家应有的对策。柏拉图首先指出;艺术创作出于人类喜欢模仿的天性。比如,床可有三种,一种是柏拉图理念世界里的床概念,由上帝创造,一种是木匠制造,第三种是艺术家的模仿品,如画家画的床。艺术家模仿的是事物的皮毛,而非事物的本质。同样,诗人为了出名,极力打动人们忽冷忽热的情感,对人类心灵深处的理性并不感兴趣。如果人类要追求幸福与道德的话,首先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凡事不能感情用事。如果让诗人们为所欲为的话,统治一个国家的不再是理性,而是人类心中燃烧的欲望。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没有艺术家位置,他们在被驱逐流放之列。
柏拉图说,“对于淫欲、愤怒与其他的一切情感,以及与人类行动不可分割的欲望、痛苦与享受等等,诗歌刺激与培育相应的激情,而不是使它们消亡;诗歌让这些激情主导人的行为,而如果人类要增加幸福与情操的话,它们应当受到控制。” 柏拉图单独提出,赞美神与名人的颂歌可以允许存在。[2]
亚里士多德指出观看悲剧表演的情感宣泄作用,但总体上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诗歌艺术观与柏拉图是一致的,把诗歌艺术放在政治的框架内,把艺术看成对真实世界的模仿。
二、中国、希腊不同社会环境孕育截然不同的诗歌
上述东西方哲人对待诗歌艺术的这一截然不同的态度反应了中国与古希腊的不同社会环境:前者长期停留在原初社会阶段,到战国时期才出现典型的二级社会,而后者在柏拉图时期早已进入典型的二级社会数百年之久。
英国著名修女,凯琳·阿穆斯特朗 (Karen Armstrong),在她的《上帝史》一书中写到:“当人们编造他们的神话,膜拜他们的神灵时,他们并非寻求自然现象的文字解释。这些象征性的故事与史前岩画是古人企图表达他们内心的惊奇,企图将充满周围世界的神秘与他们自身生活联系起来;今天的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常常为同样欲望所驱动。”[3]
阿穆斯特朗把古代的宗教与史前岩画都归结为一种人类内心的自我表达。我们这里用两个比喻来代表阿穆斯特朗与柏拉图对艺术的理解,即灯与镜子。灯用自己发出的光映照周围,并不从周围收回任何东西,这就是艺术的自我表达说。在原初社会,这种表达的对象是面对面的同伴,即原初社会情感交流的过程。镜子只能映照周围,自周围获得事物的影像,并不给出任何东西,这就是柏拉图的艺术模仿说。我们以为镜子照出的影像细致而真实,但在柏拉图看来,那只是肤浅的表面认识,有如画家画的一张床。柏拉图认为,古希腊城市的市民们有如坐在一个岩洞里人,面对内壁,脚又被锁住,不能转身,只能看到由洞口射进来的光落在洞壁上以及洞口处木偶或动植物的投影。即人类看到的世界远非世界的本质,只有哲学家才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柏拉图的哲学家也正是镜子,映照世界的意思,只不过更准确、更接近真实罢了。
专门研究西方浪漫主义时代的美国文艺评论家,亚伯拉姆斯 (M.H. Abrams, 1912- ) 于1953年发表《镜子与灯:浪漫主义理论与文艺批评传统》一书,提出镜子与灯的概念。镜子代表作家对现实世界客观理性的如实反应,有如科学家用实验观察来揭示客观世界一样;浪漫主义时代作家有如一盏灯,照亮人类的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亚伯拉姆斯认为西方十八世纪文学是镜子,而十九世纪文学是灯,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是由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浪漫主义运动,使诗人变成一盏灯,他们开始用内心发出的光照出一个新的世界。[4]
这里必须指出,镜子与灯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比较而言。本文借用亚伯拉姆斯这一概念来概括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种强调对外界的认识,一种强调内心的表达。我这里用它来阐述原二级社会与原初社会艺术思想的不同,进一步代表西方与东方传统文化的不同。
原初社会的业余时间用于自我放松与怡悦,这和其他动物是一样的。幼年哺乳动物都有嬉戏玩耍的行为,人类将这一嬉戏玩耍的天性保留终生,这也包括柏拉图所说的人类模仿天性。总之,人类的自我怡悦有自我超越的成分,这里称为广义的美学追求,即阿穆斯特朗的宗教、岩画以及原初社会所能有的业余诗人、艺术家、音乐家的行为。
原初社会的这种艺术性的自我表达首先是集体性的,是面对原初社会其他成员的。中国古代曾栖息有大量长臂猿,它们群居,鸣叫声可传播二三里之远,这里呼,那里应,此起彼落,颇似一个大合唱,常为诗人描写。原初社会的人类艺术也是这样,面对社会与同伴,以激起共鸣,所以使用的社会能接受的形式,并有自我约束成分,但这是人类天性的自然表达,并非圣人的设计。
二级社会是建立在原初社会的业余时间之上的,一切与社会的既定方向一致,一切都与既定的价值系统相协调,结果是无不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原初社会的业余时间使用是人性的展现,二级社会的业余时间留给人类文化的创造,功利主义与自我实现的追求等等。在财富积累与战争文明的大前提下,强调科学与理性,原为业余时间的艺术也带上认识的色彩,即镜子的功能。古希腊的艺术家们开始以写生练习基本功,所以我们今天也惊叹古代西方人物造型的逼真。这种艺术造型的逼真是镜子功能的写照,不见于原初社会。
必须强调指出,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自我表达是不一样的,这有如中国《诗经》一类的古典诗歌,即使西方一般人也能读懂,因为那是原初社会人类的表达方式;很多现代诗歌,一般人很难读懂,因为那表达是二级社会一个独立的个人,这种个人对周围世界产生怪异的感觉,并感到自身的孤独。
以上是一个简略的概述,至于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定义与分野,以及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业余时间使用不同的详细论述,请读者参看前文。[5,6] 以下叙述中国与西方古代诗歌艺术的不同。
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对孔子所谓“思无邪”的话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所表达情感的纯正,一种解释为情感的真实。这两种解释合起来就表示:只有纯正的情感才是真实的,不纯正、不真实的情感就是邪与淫。有一次,子夏问孔子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为也?” 孔子回答说,“绘事后素”, 就是说本色在先,绘画在后,艺术是要表达真实的,而这种真实是美目巧笑的绚丽,而非生活中丑陋的一面。其结果是温柔敦厚,情感中正,孔子认为《诗经·关睢》符合这一理念, 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侑》)
这样的艺术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孔子曾多次叫儿子伯鱼学诗,一次说,“不学诗,无以言。”又有一次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立也与!”(《论语:季氏》;《论语:阳货》) 有的学者论证说,孔子与学生讨论时有音乐伴奏。《论语·先进》中叙述孔子与子弟们讨论个人志向时,孔子让曾点说说他自己的想法时,曾点“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 即曾点停止弹瑟,先作收尾,然后铿的一声停止,放下瑟坐起来。这样一个诗书礼乐的环境无疑有利于陶冶与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也就是真实纯正的情感。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中正美好的真实是人性的内涵,并非虚伪,更非政治炒作。在古代原初社会中也偶尔有丑恶事件发生,而这些事之所以丑恶,是人类生来有厌恶它们的天性。这种天性的厌恶之心足以使人们淡忘这些事件,就更不会让它们出现在诗歌艺术创作之中了。作者曾将人类心理体验分成生物、社会、文化、智慧、精神与宇宙六个层次,作者将艺术归于只有好坏没有对错的精神层次,这是一种提升,是物质生活的升华,并非现实世界的镜影像。既然精神层次的表达之敦厚中正符合人类的天性,中国古代缺乏二级社会的建制,孔子这种艺术思想就源远流长,来自上古的原初社会。[6]
中国最早的艺术理论的记载是尚书尧典虞舜的话,他对乐官师说,“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段话的翻译为:“我任命你来主持声乐,教导我们年轻一代。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谨慎,刚强而不刻薄,俭朴而不傲慢。诗歌表达情志,歌咏是言语的拉长,声乐要谐和歌咏节奏,音律要谐和五声,八种乐器的音调协调,不失去相互的秩序,神与人就会和谐统一了。”古时人话语简单而缓慢,与现代语言相比,更富有诗意与音乐性。
虞舜的艺术思想与孔子完全一致,他提到语言拉长与神人合一。现代科学证实,语言的拉长有助于思维的放缓,而思维的放缓有助于情感的激发,这是诗歌较散文精炼而多重复的原因。如每一二秒钟就换一个镜头的影视,能使人完全忘掉自己,无法出现情感的感受。当人们进入一种和谐中正的情感与心态时,也就近于庄子的坐忘与尼采的人与大一的汇合。这也就是作者所提到的原初社会深层意识层面的整体性,由于泛灵论的影响,这种深层意识层面上的整体性可以涵盖周围事物,即人与周围事物在心灵上的整体性。如两三岁的儿童会将周围事物想象成和自己一样,有同样的思想与需要,认为自己的小枕头也要找妈妈,需要把它与大枕头放在一起。这不过是这种原初社会深层意识层面上的整体性在人体语言上的表达。[7]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艺术有本质的不同,之间也有许多联系与相似。这里打一个比方,一个小孩子玩积木,他会用积木垒成不同事物的模型,这种模型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仅有娱乐价值的纯艺术品。孩子不是非要做成某一模型,而是做成某一模型使他心神怡悦。如果成人来控制孩子玩积木的活动,他们首先引入奖惩制度,以孩子所垒积木模型的复杂程度给予不同的奖励,等他们发现这一奖惩制度的作用很有限时,他们开始将积木模型的复杂程度与孩子的物质生活直接联系起来,即将孩子能否能继续生活下去以及物质生活的质量与所垒积木模型的复杂程度直接联系起来。在残酷的淘汰制下,积木对孩子来说不再是一种纯娱乐活动,积木模型虽然还保留原来的艺术形态,但却在评判人员的标准下急剧向无限复杂的方向迈进。我们有了这样的眼界之后才能了解古希腊艺术的根本不同,因为古希腊文明从典型的二级社会开始。
《诗经》的作者全部是业余的,而古希腊最早的诗人荷马就是一位职业诗人,这些诗人首先要与其他职业诗人竞争,然后才能靠诗歌赚取自己的生活费用。如果这些职业诗人也象虞舜与孔子一样主张诗歌要敦厚中正,在雇主面前就缺乏竞争力,他们一定要抛开艺术真实性的束缚。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因为古希腊戏剧台词用诗歌形式,剧作家们也是诗人。《云》的人物中有现实生活的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显然脱离了真实,将苏格拉底做了喜剧式的丑化,以增强舞台效果。苏格拉底被说成为赚钱而包揽诉讼的人,用诡辩与谎言欺骗青年,而真实的苏格拉底强调自己与当时的所谓智者不同,他仅仅为追求真理而已,所以苏格拉底教导青年是不收费的。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这种高尚的志趣可能一无所知,只知道迎合世俗爱好。苏格拉底在判他死刑的法庭前答辩时讲到此事,认为起诉者受了阿里斯托芬的影响。苏格拉底的死刑原因虽然复杂,由501人的陪审团自由投票来判刑,喜剧《云》在雅典居民中的长期影响无疑起了作用。
二级社会有许多种,不同的阶级追求不同的政治。《诗经》中也有埋怨牢骚之作,但怨而不怒,不失为原初社会自我表达大合唱的一曲,缺乏明确的政治含意。古希腊的诗作常指向不同的政治方向。公元前第六、第五世纪,希腊社会急剧变化,由贵族政治转为平民政治。阿尔凯乌斯、萨佛、基格尼斯(Alcaeus, Sappho, Theognis) 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三位被流放的诗人,他们的诗作充满对过去贵族生活的留恋,对平民政治的谴责。他们知道,贵族政治较为民主,因为贵族有政治素养;平民政治的早期只能是专制,因为平民对政治管理缺乏足够的认识。以上三位古希腊诗人极力贬低专制主义政权。相比之下,战国时期的流放诗人屈原,抱怨的不是物质生活的差异,而是刚刚出现的二级社会现实,屈原的政治理想既不具体,也不现实,却充满艺术性的幻想,这是因为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原初社会的缘故。
二级社会的个人不能再像原初社会那样与社会进行心理与情感的沟通,二级社会的整体性有赖于社会成员对统一目标与方向的认同。二级社会的个人变得无限孤独,他们要找回原初社会深层意识层面整体性的那种感受,宗教是一个途径,艺术是另一个途径,即上面提到的人神合一、与大一汇合等心理感受,二级社会通过艺术这一媒介达到不见面而有心理与情感上的沟通。因而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艺术重要不同之一是细节描述的有无与程度。只有详细的细节描写才能把千里之外的人形象地展现在眼前,比如一位妇女如何打开情人来信这样一个细节就可以有数百字的描写,影视可以用十数个特写镜头来展现主人公的复杂心情。中国早期文学作品《诗经》与《山海经》缺乏这样的细节描写,而古希腊的早期文学作品充满这样的细节描写。由于篇幅考虑,本文不能引用作品内容来证实这一点,仅以《诗经》与荷马史诗长度来说明,诗经三百余首加在一起才三万多字,荷马史诗仅两首,分别讲述一场战争与一个英雄战后回家的故事,这两首诗翻译成汉语要有数十万字之多。可见在细节描写上,《诗经》、《山海经》与荷马史诗有天渊之别。
由于人类的天性,某些生活中的现实是不提升到精神层次而表达成语言的,二级社会打破了这一人脑过滤功能。其一是淫秽细节的描写,《诗经》遵从敦厚中正的原则没有淫秽的内容,而淫秽似乎是古希腊生活的一部分,诗歌也不能幸免。古希腊绘画雕塑就有淫秽内容,如一群男人相互性交的场面,如一个公元前二世纪的铜像塑造的是一个驼背人公众场合手淫的造型。古希腊诗歌对男人聚会性交场面也有直接描写,不便引用。尼采用太阳神代表梦幻中找回自我,用酒神代表醉后狂欢与放荡,尼采举两个诗人来代表太阳神与酒神,这就是荷马与比荷马稍晚的阿尔基罗楚斯(Archilochus),而阿尔基罗楚斯是一位有名的流氓诗人。因为与他订婚女友的父亲不同意这件婚事,婚约被取消,为了报复,阿尔基罗楚斯用最淫秽的语言做诗来描绘他的女友以及女友的妹妹。这些诗歌的流传使得女友一家人无法生活下去,一家三口人全部上吊自杀。这也说明对淫秽内容的忌讳是古今中外一样的,也让我们理解柏拉图为何主张取缔诗歌。
三、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迁与诗歌艺术思想的转化
中国于战国时代逐渐进入二级社会,与古希腊社会仍有较大区别:中国缺乏发达的商业文明与强大的中产阶级,这使二级社会独立个人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中国此时毕竟已经进入二级社会,对诗歌艺术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让我们看一看着名儒家大师孟子与荀子对诗歌的不同态度。孟子与荀子显然已经失去了孔子那种全力推崇诗歌艺术的态度,不再推行所谓诗教。在他们眼中,诗歌艺术仅仅是文字艺术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载体。孟子虽然主张人性善,但也认为二级社会的人与人有本质的不同,并不能一概而论。
《孟子·万章下》中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这里显然认为认识了解当今世界上的杰出之士还不够,还要了解古代的杰出之士。要了解古代的杰出之士,要颂其诗,知其人,还要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孟子在《尽心上》中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对战国政治采取否定态度,所以王天下的事与他无关,孟子上面的话完全是一个二级社会独立个人独乐其乐的形象。在孟子心目中,人已经成了独立的具有不同思想的个人,诗歌只能代表作者个人,所以读诗还要了解诗人本人与其生活的时代。
荀子在《劝学》篇说过“《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他讲的是《诗经》,并非战国时代的诗歌。荀子在《乐论》中说过,“乐合同,礼别异”,主张音乐能使人们沟通情感,从而达到团结统一的目的。这是因为音乐在表达个性上不如诗歌,尽管荀子也同时强调“君子耳不听淫声”。荀子写了《成相》一篇通俗诗歌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成相是古代一种文艺表演形式,荀子以这种形式写作,显然利用它为人喜闻乐见的特点,向普通人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与孔子不同。诗歌可以用来宣扬不同的政治主张,当然在可以取缔之列。荀子在《儒效》一篇中说,雅儒主张“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仪而杀诗书”,荀子对雅儒表示认可,说“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所以荀子认为,诗书艺术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取缔的。
法家人物商鞅与荀子学生韩非都主张焚诗书以钳制艺术自由的, 这就与柏拉图主张有些接近了。荀子的另一个学生李斯当权就真地焚书坑儒了。商鞅、韩非主张为了富国强兵,柏拉图主张却是为人类设计理想国。柏拉图限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战争文明的大前提下设计的,所以对人性作了残酷的限制,包括诗歌艺术的追求。从道家看来,柏拉图的理想国根本算不上理想。商鞅、韩非与柏拉图一样都忽视了人类二级社会多元协调的现实,过多强调价值的一体性。
孟子在《离娄下》中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这里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从诗歌创作转向历史散文的过程,这当然是相对而言,孟子可能不知道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出现于战国。孟子说的是个人创作,作为国家文献的书、史以及《周易》等只能是散文体。诗歌与散文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富于情感,后者富于理性,前者似灯,后者似镜,这正是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艺术思想的区别所在,当然这种艺术思想也会影响社会人群的思维方式。所以孟子所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也代表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由原初社会转变为典型二级社会的这一深刻社会变革。在原初社会中,人们面对面,说话含有情感,像灯一样相映成辉,与诗歌近似;二级社会中,人们面对无数的陌生人,说话要克制感情,象镜子一样客观,与诗歌相去甚远了。我们今天如果看到一个为人温柔敦厚的社会,绝不会像孔子那样说,这是“诗教也”,因为二级社会人的行为与诗关系不大了。
这里应该指出,老子、孔子处在春秋末年,是二级社会出生前的阵痛期,尚未出现典型二级社会,老子与孔子思维方法仍有诗歌特点,《道德经》以韵文写成,与论语一样都是格言式的,并且夹杂感情成分,即使孔子编订的《春秋》,也是微言大义,并非事事都直说的。
四、对后世的影响
同样为了社会的健康与人类的幸福,孔子与柏拉图对诗歌艺术采取了不同态度。今天的社会虽然空前的复杂,用以连接社会的通讯技术登峰造极,但仍系二级社会,故今天的艺术作品与古希腊艺术相比较,有许多相似之处,很难说今天的艺术比古希腊更高级一些、更复杂一些。作为二级社会的艺术,古希腊的艺术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诗经》《山海经》作为原初社会的艺术,和今天艺术作品似乎有很大的差别,但与现代人也有相通之处。
据说,野生的牛一生都走着同一条路:早晨起来慢慢腾腾地到草地上吃草,傍晚到附近小河里喝水,之后到树林里过夜,如此周而复始。生活在二级社会的人类思维也这样,他们一代一代地重复开始年代的思路。东西方的传统诗歌艺术正是这样,中国继承《诗经》传统,像灯;西方继承荷马史诗传统,像镜子。
哈佛大学专门研究比较文学的斯蒂芬·欧文教授说:西方文学概念产生于古代史诗与戏剧,讲故事与表演故事;西方诗歌也这样,讲述故事,创造场面与视野,通过假面具来讲自己。这种诗歌是少数专业诗人面向读者大众。欧文认为中国诗歌完全不同,中国诗歌是一种交友与陪伴艺术(companionable art), 面对的是知音,就是能体会同一心境的人。中国诗歌也可以说是谈知心话的一种高级形式。[8] 一句话,西方传统的诗歌艺术更像镜子,创造场面与视野不过是人造二级社会创造场面与视野的一部分;中国传统诗歌继承原初社会情感集体表达的思路,只是原初社会表达对象是其他社会成员,而在二级社会的无数陌生人面前,表达的对象只能是知音。
即使屈原的长篇诗作也能难说有丝毫的镜子作用,《离骚》不能照出了我们社会那些难以看清的细节,也没有描画出一个让人可以模仿的特异世界,总之读《离骚》是情感的共鸣,对现实生活并无指导意义。此后二千余年,中国诗歌主要表达个人的感受,对二级社会现实的揭露留待政论文章。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家采取以原初社会为模板来治理二级社会的政治途径,另一方面是秦汉以后的大一统专制王朝给文人留下很少的自由思考的空间。相反,他们单调的生活与险恶的政治环境迫使他们向传统道家思想寻求心灵的安慰。这有点象西方基督教徒每星期日向上帝集体祈祷,能让二级社会孤独的人们找回原初社会深层意识层次上社会整体性,他们在祈祷的那一刻,真的好像全体与一个更高大的实体上帝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国古代诗歌也有类似作用,让作者与读者感受到那一盏盏心灵的灯,相影成辉,连成一片,自己仍是这一个心灵整体的一部分。这当然与原初社会的诗歌艺术不尽相同,如陶渊明的诗作是典型的田园诗歌,除了自我表达外,他的诗时常流露出对二级社会的抨击,标榜清高自许,实际上已经构成二级社会的一种价值观。尽管如此,中国传统诗歌从风格到内容还是与原初社会诗歌相近,而与西方传统诗歌不同。中国传统诗歌的主流是表达诗人一种宁静高远的意境,一种人类永恒意识的深层感受。
古希腊之后的罗马帝国全面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巨人之后不容易有巨人,罗马艺术相应逊色。欧洲中世纪艺术成了基督教的附庸,只有文艺复兴重新发现古希腊与罗马时期的艺术,世界才开始现代化的历程。近代西方思想史的演变是先有反基督教神权的启蒙运动,而后才有浪漫主义运动。专门研究西方浪漫主义时代的美国文艺评论家,亚伯拉姆斯才提出镜子与灯的概念来概括这一人类重回自然与人性的历程。自十九世纪初开始的浪漫主义运动使西方诗人重新变成一盏灯,但这是现代二级社会的个人,是人为之人,与中国传统诗歌强调天然之人不同,所以西方现代诗歌有怪诞与难懂的名声。
中国传统诗人继承了《诗经》敦厚中正的传统,屈原那种凝滞式的嘶嚎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二级社会多变而又复杂,用镜子照出前面的可能道路实为必要,象莎士比亚那样影照出社会百态的诗人,中国可以说至今没有。西方诗歌中那种对人生悲剧性与社会恐怖性的认识,在中国传统诗歌中没有丝毫的影子,那些消极因素可能被误认为禁忌被过滤掉了。
五、其他艺术
艺术发展较社会有着更大的自由发展的余地,就更容易沿著两千多年前开始的路子走下去,结果东西方其他传统艺术的区别也大多可以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不同来解释。
路易十四对他的宫廷画家说,“我如此信任你,把人世间最神圣的东西,我的名声交给你。” 只有在二级社会中艺术才有如此的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同样,只有镜子里的不同影象才会带来这样差别巨大的社会效果。中国历史上宫廷画家也给皇帝画像,显然是理想化的形象,是画家心目中的皇帝,又因为中国历代皇帝画像似乎都一个模样,这是一个传统形象,并非一个画家所特有。就是说,连皇帝画像也近似于灯,由画家群的集体心态决定。我们的国画艺术原则有所谓“澄怀观道”、“气韵生动”、“境生象外”等说法,强调神韵,忌讳西方传统艺术式的表面相似,结果表达的只能是画家自己的精神与神韵。他们是在用山水、鱼虫与花鸟等作为符号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传达的不是画家一个人的,而是一种人类永恒意识的深层感受,一种传统的宁静高远的意境。
作者曾指出,由于古希腊城邦之间战争与二级社会与陌生人打交道等社会境遇,西方绘画与造型以人物为主,几乎不知道画别的景物,风景画要到十七世纪才在荷兰首先出现。[5, 第305-317页] 古希腊的人物造型一开始受埃及影响,但很快走向进一步写真,摆脱理想化的痕迹。我们今天看到古希腊的人物雕塑,为那衣着条纹的细腻与颜面的逼真所感动。这种传统到了达·芬奇的肖像画“蒙娜丽萨”与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雕塑“大卫”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据说照相技术发明给这种镜像艺术思想带来困惑:画家要从此失业了?在浪漫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下半页,出现所谓印象派画家,他们用粗笔划画所谓印象,开始被讥笑为没有完成的绘画草稿。认真讲,印象画仍属镜影象范畴,只不过增加了几分画家的主观色彩。梵高(1853-1890)被认为是表现主义画派的鼻祖,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颜色与形体表达自己情感的西方画家。在我看来,梵高画所传达的情感不过是一种人生的困惑,还谈不上离奇。梵高以后的表现主义画家大多以奇特著称,他们想表达人类存在本身的荒诞与惶恐感。从古希腊视觉艺术开始,两千多年后到梵高才回到原初社会艺术表达的思路,但表达的二级社会个人意识的表层感受,与原初社会艺术表达人性的深层意识不同。
据美国克拉尔科大学中国社会史专家若波(Paul S. Ropp) 研究,中国与西方小说的发展历程与年代都十分相似。如二者都在14-18世纪商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伴有小说的迅速发展,都在16-19世纪出现小说的自传化倾向,二者都最后出现以抨击主流社会为己任的小说创造倾向。若波所指出的东西方小说的不同大多可以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不同来解释,这里不准备全面评价,仅举例说明。例如,中国小说的眼光放得长远、社会视野广阔。这完全是因为原初社会只有一种,从时间与空间上都是均匀一致的,又基于人类本性,而二级社会是人造的,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不断变化的。中国人内心深处还有原初社会的理想,所以眼光长远与宽广。 与西方小说比较,中国小说结构松散,缺乏线性发展的故事,高潮不在结尾而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处。线性发展 是二级社会的事,原初社会本身没有方向性,所产生的故事也结构散漫而注重高潮后的回光反照。
与西方小说比较,中国小说缺乏悲剧性与性格境遇极端化的英雄。人类文明化的生活具有悲剧性,即二级社会与人性相违背所导致的生活悲剧性,复杂险恶的二级社会环境需要极端化的英雄解决各种不可解决的困难。原初社会生活稳定而单一,人们需要的慈爱与公正,所以中国小说的英雄人物具有中庸的美德。[9]
最后我想讲几句有关《红楼梦》的话作为本文结语。《红楼梦》的主体思想是以原初社会的平等与亲情等价值观为理想,对二级社会的价值观进行无情的抨击。亲情与平等是原初社会的主要价值观,而在二级社会中,正是女人较男人、年轻人较成年人、爱好艺术的人较讲社会实用的人更少受二级社会思想影响,《红楼梦》理想化的人物正是女人、年轻人、爱好艺术的诗人、戏子等。《红楼梦》所展示的悲剧是原初社会在二级社会倾压下逐渐消亡的悲剧。林黛玉与贾宝玉虽然可能有生活原型,但林黛玉与贾宝玉的艺术形象只能是虚构的,二级社会的现实中已不允许这样的人物存在。林黛玉是原初社会的理想人物,薛宝钗是二级社会的理想人物。薛宝钗的悲剧是二级社会本身的悲剧,也就是西方式的悲剧。林黛玉的悲剧才是原初社会理想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是心灵之灯在无数镜子的倾压下熄灭的悲剧,也是文明社会带给人类的悲剧。以西方文化传统来看,林黛玉的悲剧相当亚当、夏娃执意要返回纯真的伊甸乐园所造成的悲剧,而不是他们子孙在二级社会中互相残杀所造成的悲剧。
文献
[1] 袁行霈(2005):《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6页。
[2] Stanley Rosen (2003): The Philosopher's HandbooK: From Republic by Plato, p201-215.
本文所引柏拉图著作均作者本人自英文翻译所得。
[3]. Karen Armstrong (1994): A History of Go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4, p5.
[4] M. H. Abrams (1953):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5] 柚声:一个审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新视角,见本网站《学灯》第7期
[6] 李柚声(2006):中华道学的一个新解释。加拿大,伦敦:道学康复中心,2006。
[7] 柚声(2008):五服制度与东西方早期文学思想。学灯第8期
[8] Stephen Owen (1990): Poetry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P. S. Ropp ed, Heritage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9] Paul S. Ropp (1990): The Distinctive Art of Chinese Fiction. In P. S. Ropp ed, Heritage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请您注意:
- ·自觉遵守:爱国、守法、自律、真实、文明的原则:《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