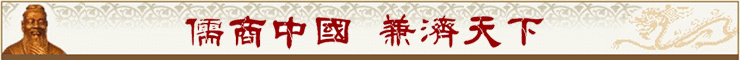《孔子家语》佚文献疑及辨正(宁镇疆)
《家语》之为伪书,久成定谳,但近些年来随着与之相关的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尚不足以完全憾动人们的传统看法。究其原因,不只是由于所谓王肃伪造之说久有影响,还在于今本《家语》十卷(两唐书亦如此),而隋志所载却是“二十一卷”:今本仅约当唐时的一半,这似乎意味着即便是王肃的“伪造”之书,到今天也是劫后余生、残缺不全了,这更加深了人们对它的怀疑。像明代何孟春即云:“司马贞与师古同代人也,贞作《史记索隐》引及《家语》,今本或有或无,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肃之全书矣。”“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以此而推,此书同事异辞,灭源存末,乱于人手,不啻在汉而已,安国及向之旧,至肃凡几变,而今重乱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需要说明的是,今之王注本十卷《家语》何氏并没有见到,他所见到的只有元代王广谋的节略本,故而其关于《家语》“重乱而失真”的评价也可以理解。不过,即便后来宋本王注《家语》十卷多有刊刻,也仍然改变不了学者视其为“残本”的评价,像明代黄鲁曾就说:“考之《艺文志》(即隋志,笔者按)有二十一卷,王肃所注何乃至宋人梓传者止十卷?已亡其太半”姚际恒也说:“今世所传《家语》,又非(颜)师古所谓今之《家语》(即唐本)也”。
假如今本《家语》卷数相对于唐本有一半之失,其佚文自不在少,故而清代以来学者开始着手《家语》的辑佚工作。清代孙志祖在撰《家语疏证》之余,亦辑有《家语逸文》,后来王仁俊编《经籍佚文》,即全盘吸收了孙氏的辑佚成果。不过,让人颇感蹊跷的是,孙氏所辑“佚文”仅有三条,这与《家语》卷数的“亡其太半”相比,也未免太少了。不但如此,细辨孙氏所辑三条,其“佚文”的性质亦间有可商。另外,程金造先生编著的《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对《索隐》所引之书多有辑考,其中亦有涉及《家语》者,有几处在程氏看来“今《家语》无此文”,即为“佚文”,然细加检视,这几处要说是“佚文”亦多有问题,今综合两书所见,对其中“佚文”略加辨正,希望能对我们认识《家语》一书的流传有所补益。
孙志祖所辑第一条出自孔颖达《左传正义》,该书卷一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此条作为“佚文”是颇可疑的:如此处真为《家语》之文,其何不径引《家语》本书,而据《严氏春秋》为说?南朝的沈文阿属转引《严氏春秋》,且不云《家语》,可能在当时的《家语》中就无此内容。王仁俊亦云:“《严氏春秋》已佚,仅引见于他书,此条严氏所见《家语》,盖非王肃所伪造者”。 “非王肃所伪造”,意味着在王氏看来此条并非王注本《家语》之文。那又是何书之文呢?笔者以为,如果此条当初真的系《家语·观周》篇的内容,那它就应该是很多学者提到的“古家语”之文。这种“古家语”即汉志的二十七卷本,它与经孔安国整理、王肃作注、流传至今的今本《家语》宏观上判然分属两大版本系统。晚近以来的出土文献,都向我们透露了这种“古家语”的若干信息:比如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所出简牍以及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所出《儒家者言》。阜阳双古堆简牍下限不会晚于西汉文帝十五年即BC165年,而定州八角廊《儒家者言》汉简则为宣帝时物,再到成帝时期的刘向整理并著录,这说明“古家语”终西汉一世始终是流传不辍。著《严氏春秋》的严彭祖属西汉中期人,曾与颜安乐从眭孟受《春秋公羊传》,宣帝时立为博士。应该说他得见“古家语”并加以引用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古、今两种《家语》虽然名称相同,实际上内容差别是很大的。从今本《家语》的后序看,孔安国整理、重编《家语》的初衷之一就是有感于“《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因此他的整理、重编就肯定有刊正文词、甚至重组章句的地方。孔衍奏文中也称安国整理的本子“典雅正实,与世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就是说,孔安国已经以自己整理的工作,使得《家语》较之他的材料来源面目全非了。《严氏春秋》所引既属“古家语”系统,而孙志祖及今人所辑《家语》“佚文”,则是针对今本《家语》,所以此条作为“佚文”就是有问题的。
孙志祖所辑《家语》佚文第二条出自孔颖达《诗·大雅·皇矣》正义,其引《家语》:曰:“纣政失其道,而执万乘之势,四方诸侯固犹从之,谋度于非道,天所恶焉”。此条的确不见于《家语》本文,故而范家相也说:“今本及肃注并无此语,盖肃之《家语》失传,亦良多矣”。不过,细加辨析,此条虽不见今《家语》,但却与今之《家语·辨乐解》篇“众夹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国”下王肃注接近,王氏注云:“夹,武王四面会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与纣同恶也。”所谓“四方”与 “四伐”,“诸侯固犹从之”与“与纣同恶”都非常接近,考虑到古人引书多节引、暗引之例,此条很可能就是引的王肃的注。这里所说古人引书节引、暗引之例,在唐人的著作中是非常突出的现象。所谓“节引”,是指古人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词句必较,而是跳跃性地拈取某句中的若干部分来引用。如《初学记》中就曾两次引到《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对子羔的记载,但两次相比即详略有别:《初学记·卷十九·丑人第三》引《家语》曰:“高柴字子羔,长不过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知名孔子之门,仕为郕宰”,又《初学记·卷十九·短人第五》引《家语》曰:“高柴字子羔,不过六尺,为人笃孝”。由于所引各有侧重,我们可以看出具体的引述体现出明显的“选择性”,我们显然不能以这种引文与今本的差别就说存在什么“佚文”或“衍文”。而所谓的“暗引”则更为灵活,引述者可以完全不必拘泥于著作原文,而是以自己理解之后的意思表述出来,从文句上看可能与原文几无对应,但意思上却又让人有种“似曾相识”之感。如《仪礼注疏》卷十贾公彦疏引《家语》云:“定公假马於季氏,孔子曰:君於臣有取无假。”此条对应今《家语·正论解》,其文曰:“孔子适季孙,季孙之宰谒曰:‘君使求假于田,特与之乎?’季孙未言.孔子曰:‘吾闻之君取于臣谓之取,与于臣谓之赐,臣取于君谓之假,与于君谓之献.’季孙色然悟曰:‘吾诚未达此义.’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虽然在文句上差异很大,但意思上却并无二致,这显然是引者在对《家语》此文理解之后以自己的语言表述。因此,前文提到的孔颖达《诗·大雅·皇矣》正义对《家语》的称引,当即是“暗引”王肃的注。
孔氏《正义》既是对王肃注文的称引,那为何又径称“家语”?这实际上牵涉到唐人引书的另一个习惯,那就是凡引某书,也往往将其注文俱称某书。如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五引《家语》云:“今池水之大,谁知非泉焉”,此处实兼引《家语·致思》篇“譬之污池,水潦注焉,雚苇生焉,虽或以观之,孰知其源乎?”本文及王肃注。如果我们搜检唐人所引《家语》,目光只盯着《家语》本文,就会把此类注文视同佚文,实则不然。
孙志祖所辑第三条出自《列子》张湛注。《列子·汤问》:“荆条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盈车之鱼”,张湛注曰:“《家语》曰:‘鲲鱼,其大盈车’”,今遍检《家语》及王肃注,于“盈车”之鱼,的确未见。不过,今《家语·屈节解》有云:“渔者曰:“鱼之大者名为鱼寿,吾大夫爱之;其小者名为鱦,吾大夫欲长之”,此与张注相近。不过,即使此条确为今本《家语》佚文,那也不是由于由“二十一卷”到“十卷”这样的篇卷刊落所致。因为很明显,张湛属晋人,远在唐以前,其时《家语》之篇卷形制虽不能晓,要之无涉所谓由“二十一卷”到“十卷”这样的篇卷损伤则是事实。
、程金造书(以下简称“程书”)第131页提到《索隐》有云“姚氏按《孔子家语》云,子武生子鱼及子文。子文生最(实当为“樷”),字子产”,程氏云:“案今《家语》无此文”。笔者按,此条出自《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蓼侯”条,据《史记》云:“(高祖)六年正月丙午,侯孔藂元年”,司马贞《索隐》于此云:“姚氏案,孔子家语云……”。此处虽不见于《家语》本文,但却见于今《家语》后所附王肃作后序,其中对孔氏世系传承线索有详细交代,其文略谓:“……子武生子鱼名鲋,及子襄名腾,子文名祔。子鱼后名甲。……子文生最,字子产,子产后从高祖,以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谥曰夷侯”。王氏此处所云封为“蓼侯”的“子文”行状,与《史记》大致相合。考《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蓼侯之封,是因为他“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砀,以左司马入汉,为将军,三以都尉击项羽,属韩信”,故而“功侯”。司马贞《索隐》于此云:“即汉五年围羽垓下,淮阴侯将四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是也”,甚是。此条既见于《家语》后附王肃所作后序,我们同样认为它不能算作佚文,其性质与上文我们说唐人把王肃之注亦当“家语”称引的习惯类似:他们同样也把今之《家语》所附孔安国及王肃的序径称“家语”。值得注意的是,现今的王注《家语》传本中,在篇卷格局上都是在后序结束以后才题“孔子家语卷第十”作为结束的标志,而并不是在《家语》正文末尾处标著,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它提醒我们,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将后序(也包括王注)作为《家语》本书有机的一部分来看待的(这恐怕与今之《家语》在版本上仅有王注本这一单一传本有关),因此唐人引后序就可以径称“家语”。这样看来,此处作为《家语》的“佚文”也是站不住脚的。
程书第132页提到《史记·封禅书》《索隐》有云:“《家语》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程氏云:“今《家语》无此文。”笔者按:此条《史记·封禅书》原文作:“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关于霍子侯之死,据《新论》云:“武帝出玺印石,财有朕兆,子侯则没印,帝畏恶,故杀之。”《风俗通义》与之基本相同,均主武帝杀子侯之说。但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霍去病)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居六岁,元封元年,嬗卒,谥哀侯。”可见武帝对子侯可谓宠爱有加,一如其父,“杀之”之说似无道理,而且《文心雕龙·哀吊》亦云:“暨汉武封禅,而霍子侯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霍氏父子俱年轻得志,得皇上宠幸,但却惊人一致地“暴卒”,武帝之痛并“伤而作诗”就是可以想见的,此亦足证杀子侯之说难成立。《索隐》此处实际上是据顾胤引《武帝集》:“帝与子侯家语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武帝集》所载,其实应作如下断句:帝与(于)子侯家,语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也就是说,应该恰好在 “家”与“语”之间断开,《武帝集》的意思实际是说武帝在就子侯暴卒一事安慰其家人,若将“家”与“语”相连成《家语》书,即成“帝与(于)子侯,《家语》云……”,则文义扦格,殊为不通[21]。程氏有此之失,实在于断句有误。此处“家语”既属子虚,则该条亦不成其为“佚文”矣。
程书第133页提到《史记·孔子世家》《索隐》有云:“《家语》作游过市”。程氏云:“《文选》卷四十一《报任安书》李善注引《家语》曰,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出,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于是耻之,去卫云云。小司马此引游过市,与《文选》李注所引同。”末云:“然今《家语》无此文。”笔者按,此条程氏引《文选》李善注与《史记》相参证,确有搜辑之功。但其实该条今本《家语》即有,亦非佚文。其文见今《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颜刻,鲁人,字子骄,少孔子五十岁。孔子适卫,子骄为仆,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而令宦者雍梁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颜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诗云:“觏尔新婚,以慰我心。”’乃叹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程氏此条之失,盖搜检未尽也。
程书第134页提到《史记·孔子世家》《索隐》有云:“《家语》,姑布子卿谓子贡曰”程氏谓:“案今《家语》无此文”。笔者按:《索隐》此处对应《史记·孔子世家》的原文为:“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韩诗外传》卷九之第十八章“孔子出卫(实应为‘郑’)之东门,逆姑布子卿。……”亦有与此对应一段,另外《白虎通义》、《论衡》也有与此类似记载,主要都是讲所谓“丧家之狗”的典故。韩诗明谓“姑布子卿”,与《索隐》引《家语》合。今本《家语》虽不见“姑布子卿”其人,但却也有与上述内容大致对应的部分,据《家语·困誓》云:“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或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然如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欣然而叹曰:‘形状永[22]也,如丧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可以看出,今之《家语》对应部分作“或人”,此于文法不合,当是后来由于脱去“姑布子卿”后人妄补也。此处准确地说应该是词有脱漏,后人妄补,整条内容其实并未佚失。
另外,程书第132页还提到《史记·孔子世家》《索隐》有云:“《家语》,孔子,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近,别为公族,姓孔氏。孔子(“子”当为“父”之误)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程氏于此云“案今《本姓解篇》文与此有异”。笔者按,今《家语·本姓解》篇云:“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及襄(当从《史记·宋微子世家》作“煬”,笔者按)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家语》本文是把厉公以下“世为宋卿”的这一支与孔子先世弗父何这一支都作了介绍,而《索隐》于《孔子世家》下所引,当然只能取孔子先世的这一支,所以略去“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为宋卿”就是可以理解的,这其实又是上文我们提到过的“选择性”的节引,差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索隐》所见《家语》与今本有什么不同。
综上可见,无论是孙志祖还是程书所辑有关《家语》的“佚文”,其实很少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偶有其例,也不是唐以下由篇卷刊落所致。笔者并不否认今本《家语》存在佚文,但就总体上看,其实真正的佚文是很少的。这与明清以来很多学者提出来的今本存在《家语》由“二十一卷”到“十卷”这样的篇卷损伤不成比例。此种现象对我们理解今本《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个很有价值的参照。它提醒我们,唐时《家语》分卷与今本的不同,可能只是意味着每卷所含篇数有异,并不表明今本《家语》存在类似篇目缺失这样的结构性损伤。
另外,根据笔者的研究和统计,我们认为相对于《家语》本文,今本《家语》佚失更多的其实是王肃的注。如《史记·孔子世家》“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集解》引王肃曰:“谦言窃仁者之名”。《集解》此处之所以引王肃之说,因为《史记》此处又见于今《家语·观周》:“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但我们看今《家语》此处王肃却无注,因此可以相信,《集解》所引王肃之说,当为《家语》王氏佚注。再如《史记·孔子世家》“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集解》引王肃曰:“十之,谓三丈也,数极于此也。”《史记》此文又见今《家语·辨物》,但王氏于此句并无注文,故《集解》所引王肃之说,亦当为《家语》王氏佚注无疑。再如《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索隐》曰:“谓历阶级也。故王肃云:‘历阶,登阶不聚足。’” 《史记》此文又见于今《家语·相鲁》[23],但我们看对应之处王注亦未见,《索隐》所见亦当为王注佚文[24]。细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佚失的王肃注文大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疏解平庸,了无发明。就像“谦言窃仁者之名”之于“窃仁者之号”,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出注的必要。这与王氏广为后人诟病的,对五帝、郊祭等内容的刻意求新的疏解形成鲜明对照。这些了无发明、无关痛痒的注训,不知是否是其多有佚失的原因(主观的或客观的)。另外,我们还注意到,相对于《索隐》,《集解》所引的王注佚失尤多。考虑到裴駰的生活年代要早于唐一百多年,其时他所能见到的《家语》应该较唐本更接近王注本原貌。再者,像前述张湛《列子》注所引《家语》,毕竟与今本不同。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南北朝时期所流行的《家语》传本较之今本有更大的不同。或者也可以说,今本《家语》在六朝至唐这样一个时段的变化可能要更为剧烈。而唐以来今本《家语》的流变,仅从佚文之稀少看,可能并没有像很多学者仅据篇卷格局所推测的那么大。
-
请您注意:
- ·自觉遵守:爱国、守法、自律、真实、文明的原则:《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